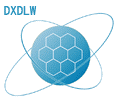首页 > 线缆专业话题
[专业话题] 西安交大曹晓龙博士的心得 《绝缘》
P:2011-12-23 09:51:32
1
序
有人说,中国的希望在西部。不知道这是科学的结论,还是宣传的口号?抑或是用以自慰的调侃占卜?反正是绝缘在上海立脚未稳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央的安排下随着交大的搬迁走了“西口”。
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教研室成立于1953年,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的那一年。当时,这个教研室归属在交大的电工器材制造系,系主任就是德高望重的电机工程权威钟兆琳教授。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按照两国的协议,帮助我国展开了156项重大的发展建设规划项目,交通大学建立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正是这其中的有关教育项目中的一项。
1956年,学校除造船、运输起重等少数专业之外,其他的各教研室开始陆续向西安搬迁。1958年初,绝缘教研室第一任主任陈季丹教授率领教研室员工来到西安,从此,我国的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的教育事业,就开始在这块文化底蕴厚重而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北重镇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硕果累累
据说,我国内迁的名牌大学中,真正成功的只有一所,这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的内迁没有让人失望。
1958年教研室迁到西安后就已开始每年招收研究生,且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都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经常有兄弟院校的教师前来学习参观。
1958年师生们与西安高压电瓷厂协作,日夜奋战一个多月,设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根330千伏变压器用油纸套管,当时由师生们发明的用环氧粘接瓷套的技术现在仍是国内的主要应用技术;与上海电缆厂、上海电缆研究所协作设计了我国第一条110千伏充油电缆。这些对当时发展国产高压电气设备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62年成立了绝缘研究室,这是原高教部最早批准成立的18个直属研究室之一。
1977年冬恢复高考。
1980年受天津市邀请 ,与天津市电缆厂、天津市电工器材公司等单位订立了大批科研合同,这些均如期完成,得到天津市的好评。
1982年,刘其昶、刘耀南教授在IEEE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绝缘测试中产生表观负损耗的理论文章,这大约是新中国学者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85年成功发起并主持举办了首届IEEE电介质材料性能与应用国际会议。
1988年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学科,定名为“电工材料及绝缘技术学科点”,是我国首批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1989年国家计委批准建设“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列入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发展项目,并于1991年开始建设,1995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
1996年主办《亚洲国际电介质和绝缘会议》
2000年再次主办举行《国际电介质材料性能与应用会议》。
这些都是我随便就能想到的,虽不至于挂一漏十,但也绝非全部。
二.“一陈、三刘、一顾”
交大讲究“大师”。
交大也讲究“饮水思源”。
提到我国的绝缘学科就不能不想到这“一陈三刘和一顾”。
陈季丹
陈先生是我们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教研室第一任主任,192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是钟兆琳教授早年的学生,也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曾留学英国,获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电工原理和无线电学的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由他在国内首先开讲的电介质物理学,奠定了这个专业的重要的物理基础,因此也被学生们尊称为我国介质物理学的“祖师爷”。他强调学生要学好外语和数学,认为学好这两个东西无论做什么都有了基础,作为示范,他可以在课堂上整黑板整黑板地娴熟地用数学来推演物理概念。
他很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并首先在我国展开氯化钠电击穿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工作。至今,电介质物理学仍旧是我们无论是从事传统的或是新方向的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与知识平台。
刘耀南
90年代初,刘先生在美国的一位同学回国来看望她,正好我也在场。她的这位同学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刘老师是我们大学班上最好的学生,再难的高等数学考试,班上没几个能及格的,她都是100分。我们都叫她中国的居里夫人。”
刘耀南先生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处人、处事、做学问。关于刘耀南先生,在她去世的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她的文章,收录在她的爱人汪人和先生编辑的纪念刘耀南教授的册子里。
晚年时她患了乳腺癌,到医院去治疗时,已发展到很严重了。给她看病的医生说:我这一生只接诊过两例发展到这么严重了才来看医生的乳腺癌病人,而且两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位是农学院的教授,另一位就是她。
在她弥留之际,病榻旁一直摆放着一台小小的单放机,不断的播放着一位亲属送给她的一盘颂经的磁带,浑厚有力、宽容平和的朗朗诵经之声,衬托着一尊祥和的遗容,让她的灵魂离开了交通大学历史上这最早的一位女教授的躯体。
刘其昶
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经济恢复的初期,“一穷二白”的中国被比喻为一张白纸。那时的交大把建设中急需的工程师作为自己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即所谓的“工程师的摇篮”。大学出来能否胜任,教材成了重要影响因素。刘先生认为我们绝缘应该有这样的一部教材,尽管当时连一本可供参考地讲义也没有。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衣食不顾,忙起来几个晚上都不曾休息,把从文献和设计研究部门搜集来的零碎数据和资料,提炼整理,编写出了我国第一本《电气绝缘结构设计原理》教科书。他同时也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本人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凝炼在这本书中。出了名的他被我国电工界誉为“套管专家”。
刘其昶先生治学严谨在室里是出了名的。他要求学生的文章中不得有错别字,要求青年教师在板书词句时,横要写平、竖要写直。画坐标轴要规范。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作学术报告,在黑板上写到一个’薄’字时,没注意将三点水写在了字的偏旁处。他立即给予指正。他认为对一名好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不是多余的。
记得在交大100年校庆那天,我们在他家里见到他时,那是一幅不同于往常的画面。他面带微笑,眼中闪着异样的光彩,稀疏的银发显然经过了精心地疏理。一身干净的经过熨烫的灰色中山装显得十分得体,胸前端正的挂着一枚鲜红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徽。他努力地挺直着快要80岁高龄的身体,一面激动地说话,一面背着双手来回地度步,俨然像是在课堂上讲课一样。他完全是把交大的生日当成自己的生日在过了。我忽然认识到,交大之所以有今天,不正是与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先生一直在和交大生死与共、荣辱相依有关吗?
刘子玉
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副博士,编写的《电力电缆结构设计原理》一书至今还是我国电缆界最有影响力的基础著作。一位在昆明电缆厂工作过的老校友曾繁学高工向我述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新加坡电力公司向世界各国招标购买高压电缆,昆明电缆厂中标并接受邀请派了我们这位校友前去新加坡做技术答辩,在答辩的过程中,新方问得很仔细,比如设计时用了什么公式,公式出自何处,计算时用了什么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哪里等。曾工为之一一作了满意的回答。末了新方发现,被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两本文献,一本是由上海电缆研究所编的电缆设计手册,另一本则是西安交通大学刘子玉先生著的电缆设计原理。曾工不无自豪地介绍道:西安交大是我的母校,刘子玉教授是我的老师。新方的技术人员细细地翻看了带去的这本已经翻看得很旧的刘先生的书,恳切地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要求:能不能将这本书留给他们?曾工说,我只有这一本了,工作中自己也离不开它。同曾工一起前去的昆缆厂厂长劝说曾工将书留下,说他自己在国内还保存着一本,回去就还他。曾工爱不释手地将书交了出去,新方的技术人员高兴得不得了!谁知到今天他也没能得到这本书。
1980年的时候,刘先生从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回国,他用自己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为教研室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在国内的海关几经周折,终于摆在了教研室里。今天来看此事似已不足为奇,可在当时这也是一件让我钦佩不已的事。一是刘先生的思想境界;二是计算机发展的速度。这台机器上印制着一个被人吃了一口的苹果图案,据说,是在鼓励人克服畏难情绪掌握电脑。要知道,当时学校只有一台读孔式计算机,是安放在行政楼里。要算题的人得先用一套冲头修改好自己的穿孔纸带,然后交给计算机室里的工作人员,过几天后再去拿计算结果。而刘先生的这台苹果机让我贴近了电脑,也贴近了发展中的新时代。
顾振军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又自费留学苏联。熟悉英、俄、德、日等多种语言。他编译过“绝缘电老化译文集”、“电介质化学”、“聚合物的电性与磁性”等时代新作。讲课时,内容丰富熟练,神情投入,声音洪亮。他的记忆力惊人。他说:学化学主要是靠记忆,理解为次,理解是为了记忆。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去问他一个俄语生词лавсон。他解释了中文意思之后,还告诉我这个词,源于法国的某某词,后传入英国变为某某词,传入俄国后就是现在的这个词。
60岁的时候他从这个让自己既留恋又辛酸的西安退休了,受聘于上海交大,后任美国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旅居美国。难以割舍的情结使他每年都要回到西安交大的绝缘来,他说过,就是自费,他也要回来,他要做些学术报告,他要把世界上最新的学术动态报告给自己人。当他听到我校电气学院正在进行教改时,就立即给刘其昶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机系做了了解,并将该系的主任的思想及建议,以及所开设课程的名称、学时等一一写在来信中,说是让我们作参考。
在他去世后,最懂他的家人多次打电话到教研室,恳请室里派人去上海主持他的追悼会。对57年反右和66年的文革仍心怀余悸的家属说,“不管他以前有什么错,希望组织上能理解他的心,也让他那从美国赶回吊唁的子女得以欣慰…”后来,是由我们绝缘毕业的校友、时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的X同志在上海主持了顾振军先生的追悼会。她高度评价了这位我国“电介质化学”创始人的一生。有一件事后来我才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在庆祝她的化工学院建院百年大庆时,曾邀请的华人学者仅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在台湾的一位院士,另一位就是我们的顾振军先生。原来从未听人提说过这些。“君子不器”嘛!
绝缘楼的花园里,鲜花和绿叶簇拥着五株专程从广州引种来的挺拔的青松,这青松的近旁,竖着一面黑色大理石的纪念碑,它以凝重的隶书镌刻着以下文字:
“我国电气绝缘学科奠基人纪念树碑
陈季丹 1907——1984
刘耀南 1918——1998
刘其昶 1918——1998
刘子玉 1927——1990
顾振军
绝缘86级全体同学敬立
2003年10月”
我想,中国不会忘记他们。
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电气绝缘是个学科交叉的专业,它吸引了许多满怀兴趣和理想的年轻人不断地加入到这个奋斗者的队伍中来。恩格斯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就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来人如果没有牺牲精神,没有“敢拿今生赌明天”的气概,我想,那是很难造就一番事业的。
74年的伍学正教授还是年富力强正当年的时候。为了发展我国的半导体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在室里和同志们一起开始了拉制单晶硅的科研工作。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但谁也没有更多的犹豫。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成果,拉出的单晶硅棒的尺寸已达到国内最好的水平!但是意外的事故发生了。单晶炉突然爆炸,近一寸厚的铸铁炉盖直然飞出,扫过他的头颅,牵引着喷射的鲜血,打在了背后的水泥墙壁上。当第二军医大的医学权威把他从死神手里硬是夺了回来的时候,已是他昏死过去4天以后的事了。
任佩余老师的爱人要生小孩了,而他自己却还在遥远的哈尔滨进修学习无法离开;俞秉莉老师是个女同志,刚生完小孩不到一月,就拿着行李去了北大参加进修。至今提说起来,他们也无怨无悔。
研究生刘利同志的课题是研究材料的老化,在那个自动化程度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这是一个要实验者与之常年厮守的工作。当人们把昏倒在实验室里的他送到医院抢救时,才知道他的阑尾就要穿孔了。
当时在室里读研究生的梅中原同志,整日沉浸在研究的思索之中,一日当他走在路上,看到两行泛青发芽的柳树,猛然一悟,“啊,却已是春天了!”
如果说绝缘这50年的历史也是用血与火、青春、乃至生命炼成的,我想,这该不为过吧。
四.活跃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
世界上的科学界都敬仰一种称之为“哥本哈根精神”的东西。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在《大学人文读本》中,有一篇杨福家先生的文章,它是这样写的, “1921年3月3日丹麦哥本哈根第一任物理研究所所长玻尔说:…极端重要的是,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的结果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青年人自己的贡献,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就会不断涌入科研工作。”
哥本哈根的气氛使人感到繁忙、激动、活泼、欢快,无拘无束,和蔼可亲。哥本哈根精神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而诞生,现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哥本哈根精神!
80年,我正在咱们绝缘室里读研究生。印象中在实验室里到处都是忙碌工作的人,见面时脸上都挂满了微笑。那时候,几乎每周在二楼的玻璃房里都举行学术报告,参加交流讨论的不仅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老先生们也几乎个个参加。讨论时发言热烈,问答不断。学术争论,尖锐而不含杂念,激烈而不失真诚。通过了讨论的文章和报告,就可以向外面的正式出版物发文章,或是在学校里印刷〈科技报告〉,出成册子。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关表观负损耗的理论、聚合物中的陷阱理论、碳化硅防晕机理与技术、高介陶瓷的击穿机理,压敏氧化锌材料等都从这里开始了国内最早的研究。而这些都成了后来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的研究成果。
那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术环境。
五.让学生的知识宽阔厚实的教学思想
耶鲁大学一位教授是这样说他们的培养目标的,一是有多方面的知识,二是知道对什么感兴趣,三是有从事工作的能力。
由于绝缘学科自身的特点,它在专业学习阶段所设置的课程涉及的学科面是比较广的,化学的、物理的、电的、材料的等。与北美大学的相应课程相比,内容要困难些,比如曼尼托巴大学的高观志教授看了我们的介质物理书就说,很难,相当他们给研究生用的教材。绝缘的专业课程几乎全部使用自己编写的教材,教材编写中除了考虑系统性、可教性外,也反映了教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例如在材料类的《电工高分子物理》课程中,起先是抓分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这条线,后来就转向结构的多重性与性能的关系这个纲。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材料的聚集态和缺陷对材料性能的影响是带有决定性的作用。表观负损耗问题的研究完成之后,尽管学术上仍存在争论,刘耀南先生还是在《电气绝缘测试技术》一书的修订版中写入了这部分内容,因为工程界已经不断地受到这一问题的缠绕。这也是当时对教材编写原则改革的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在当时,教研室编写的专业教程一直都是全国同类专业教学的通用教材。
教研室在教学环节中不仅注重课堂教学,也非常重视实验、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还在1958年的时候,教研室教师就曾带领高年级学生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下属的工厂和上海电缆厂、上海电缆研究所等单位参加新产品设计和试制工作,例如和西安高压电磁场写作设计和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根330千伏变压器用油纸套管;又如和上海电缆厂、上海电缆所协作设计了我国第一条110千伏充油电缆等。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又引导了学生将远大理想和脚踏实际的勤学苦练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样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六.领导者的艺术
办好一个教学研究中心,领导者不仅要有宏图大略,人品和威信也是十分重要的。
电气绝缘教研室成立于1953年,第一任的室主任是陈季丹先生。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组建教学队伍,拟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教案,把大学生培养成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电气绝缘工程师。陈先生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授,他领导下的顾振军教授、刘耀南教授、从莫斯科动力学院请来的曼特洛夫教授,以及1957年高教部又分配来的刘子玉教授等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学者。统领名人办好大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到56年夏,本专业就开始为国家输送合格的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1958年初,他率领教研室员工西迁到西安,同时在室内也开始了走在国际前沿的科学研究工作,并赢得了一次我们绝缘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高教部在国内的几所大学里建立的18个直属研究室之一——电工材料研究室成立。
文革之后,我们又面临着另一个艰难的历史阶段:捋顺多重复杂的关系,把同世界拉大了的教育与科研水平的差距逐步的弥合起来。或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叫做“让世界了解我们,让我们也走进世界。”
刘子玉先生时任我们电机系的主任。走向世界这个题目,对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来说可能不会在思想上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他有强我中华民族之心,有愚公移山之志,再加上不怕担待政治上的风险。他认为在学科发展的规划上一定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要知己之长识人之短,要把握机遇,从而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在这一阶段,室里有计划地吸纳了不同学科的人才,安排教师去北京大学进修量子化学,去西北大学学习聚合物化学,到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进修等。后来又首派英语基础很好的金维芳同志去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进修,就是在那里,遇到了对祖国深情依依的世界著名华裔教授高观志先生。高教授怀着一颗对祖国难以割舍的情义,和我们系、室的领导,用巨大的信心和毅力,说服了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说服了认为从来也没有举办过大型国际电工会议的中国、要办也只能办30人以下国际会议的IEEE会议主席美国的福斯特先生,还得说通从未办过这种事、把政治风险放在首位考虑的西安市的有关领导,终於于1985年,由我们绝缘室组织在西安的丈八沟宾馆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电介质材料与性能国际会议。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会议,到会的代表有400多人,境外来宾将近一半。此后,国内国外人来人往,世界开始接纳了我们。这种调息过程,滋养了内功,练就了外功,绝缘的进一步发展,渐入佳境。
在刘子玉等先生的努力下,争取到国家批准的在我们绝缘建立“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格,这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接下来的两次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的配套到位资金,就从根本上翻新了绝缘中心的硬件设置面貌。
这时候的领导高瞻远瞩,对下属关爱备至,同志们也互相照顾,同心协力,在这种大爱的氛围下,我们绝缘走到了她又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大学教师这个群体,大都希望能在一个民主、自由、关爱、和谐的环境下发挥自我,他可以在自然科学面前忍受炼狱之苦以奉献祖国和人类,却绝受不了人际之间的尔虞我诈;在这个学术水平评估还不甚成熟的时期,不平等的竞争会严重扰乱他们的方寸,以至于扼杀他们的天赋和创造力。如果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们会宁可背负屈辱退出此漩涡,无为一生,也不愿纠缠在此摩擦不休。
小时候我的心里就产生过一个问题:黄河长不过长江,水也清不过长江,为什么我们要把黄河作为代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现在,看到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看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及其他那些为生活奔波着的第一线劳动者,看到他们常常如水那样,背负着屈辱的泥沙,回避着无奈的漩涡和障碍,曲曲折折的走完自己的历程,我想,除了黄河,谁又能受此殊誉呢?
七.期盼中的未来
SARS病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巫松桢教授曾经问到一个深沉的问题:如果我国绝缘方面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谁能来回答?有没有能力来回答?
究其精神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全地球人都应反思给自己的类似问题。
2002年5月1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了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大做的题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报告。他说,未来的大学生面对着5大挑战:
1.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必须加强沟通意识;
2.知识更加实用化,应坚持广泛学习;
3.应更关注人文学科,关注人本质的内在的东西;
4.知识快速发展和更新,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应对知识慎重选择;
5.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应具有主动意识,把学到的知识释放出去。
他说,哈佛不仅重视现在流行的热门的学科,更关注一门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我们同样地关注着电气绝缘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我们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世界和正在大力度改革着的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的自强自尊意识同时袭来。我们面临着一个正在重新寻找自己信仰的社会,我们似乎是处在有序与混沌的临界之处。
今后,绝缘可能会有更大发展,那是因为它停顿过;
也可能更加辉煌,那是因为它暗淡过;
当然,它也可能灭亡,那是因为它诞生过。
我知道,这就是天命,绝缘已经50啦
catalutic master batch - 催化母料 (4) 投诉
66